我的名字叫紅 惠英紅(上)
圖文/鏡週刊
父親斷氣的那一刻,幾聲喉音,像穿過幽谷的腳步聲,惠英紅援引拿來演出《血觀音》最後一幕。說著那死而不得,斷氣不成,以為那黑暗該有多黑呀,偏偏惠英紅所召喚出來的,依然是紅。

以《血觀音》的棠夫人一角入圍金馬獎最佳女主角獎,惠英紅在劇中的心機是密室機關一關又一關,真如城裡府院重重,要人目眩。看完電影的確有全身痠疼的感覺,應該是她的眼神都有如拳腳一般實,拳拳到心,昔日打仔惠英紅笑笑說,自己真沒故意這樣使勁。
眼神裡的萬縷千絲是表面,她的用力在於更細小的肌肉群,海面之下的深處,變化微乎其乎,漾得輕巧精細,才能把告別演得真實漫長。

咽喉與瞳孔 躺著鬥戲
《血觀音》最後一幕,惠英紅貼上人造假皮,躺在病床,演她成年版小女兒的柯佳嬿不肯讓她嚥氣。此時惠英紅演的,只有聲音、呼吸與瞳孔的收放。
腔調雖是一口廣東國語,然而,惠英紅說起什麼都是力道,落著餘韻。「如果臉貼老妝了,然後不動,會浪費一場戲。我可以這樣演,多舒服就混過去了。可是這是戲裡的ending,而且導演的劇本寫女兒長大之後,不讓我死,要我長命百歲,要我受苦受難。如果棠夫人就躺在那裡,我覺得會把戲放得太低。」
「我突然想到,我爸在送到醫院時戴著口罩(呼吸器),我不知道是他最後的氣往上走,還是他的咽喉很乾,我就聽到他骨頭發出喀啦喀啦的聲音,很讓我起雞皮疙瘩,然後他斷氣了。」

她語氣這樣尋常的,彷彿是在煮一頓再日常不過的尋常晚飯。為不擾導演的局,當時惠英紅只跟收音師提醒,「待會收我咽喉的聲音。」其實她根本就沒打算舒服過一場戲。要演完全不能動,可是魔鬼就在身邊的那種害怕,要怎麼演呢?
「我的瞳孔還可以顯示我害怕。我憋住我的呼吸,因為那個儀器是真的,幾秒後它感應不到我的呼吸,就發出聲音。我憋不住氣再回來,更有那種害怕:我死不了,不能死,我還是要呼吸,還是要面對我最害怕的人。」
「我眼睛那個淚水,我一直在跟它掙扎,我不想它在中途掉下來,我一點一點晃動,讓淚水晃回去。」「當我(呼吸)再回來的時候,我眼睛裡的害怕,眼淚就掉下來,這是最完美心態的害怕。」
16樓掉下 沒死更強
惠英紅顯影一種如成魔般的心緒。我彷彿坐在一節車廂裡,見著窗外景色極深濃,包括每一片樹葉,灣仔叫賣的童年,不久前才提及的那部電影,和最不易通行的低矮密林,屬心裡荒地。
博物館羅列收藏,而惠英紅拍過的電影則保留她的一意一念。從16歲出道拍《射鵰英雄傳》,這40多年以來,她拍過百來部電影。

人生的濃與淡,她只輕輕揭開,就極有戲劇性了。「那個淡,有多淡,有多濃,其實是你心中才知道那個標準,如果你這幾十年都認識惠英紅的時候,那我以前的濃,可能真的是嚇怕你。」
服裝提供:Bottega Veneta 。造型:陳慧明 。
更多鏡週刊報導
惠英紅連咳痰都有戲 吳可熙床戲夠淫夠蕩
這才叫文武雙全 惠英紅左手武打右手畫畫好棒棒
【鏡大咖】我的名字叫紅 惠英紅(下)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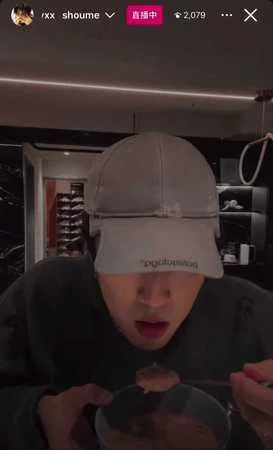








讀者迴響